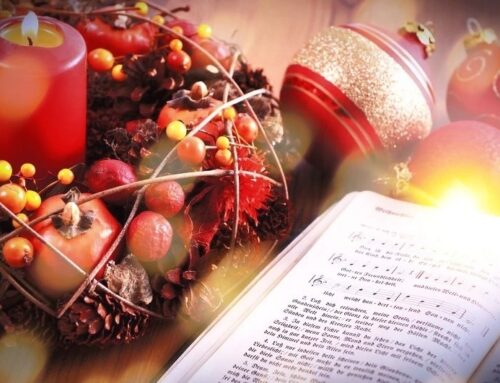19世紀,西方美術界以法國印象派作為領導,呈現出一片極為蓬勃的現象。而早在這世紀初,在英國,卻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,且承上啟下的繪畫風格 — 浪漫主義風景畫 — 它在仍以18世紀的歷史畫作為主流的畫壇上跳脫而出,並擺脫了荷蘭、法國和意大利的影響,創造出英國獨有的繪畫風格,且影響著日後法國印象派的開啟。而成就如此里程碑的,就是兩位世界級的英國畫家–特納和康斯特勃–他們同被譽為英國最著名,技藝最精湛的藝術家之一。
少年得志 與 大器晚成
約瑟夫·瑪羅德·威廉·特納(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,1775年4月23日-1851年12月19日)在瑰瑋宏奇的自然威力面前,發放他那無與倫比的創作才能。他喜歡描繪自然現象和自然災害:火災、沉船、陽光、風暴、大雨和霧霾,尤其傾倒於大海的波濤澎湃,他雖也描繪人物,但只是為了襯托不為人所征服的大自然的崇高和狂野,是上帝能力的證明。他後期專注描畫水面上的光線、天空和火焰,減少描畫實物和細節,為印象派開闢道路。
堅定志向 努力不懈
康斯特勃家境頗豐,父親是個磨坊主,不同意兒子以繪畫作為他的終身職業,希望他能成為一名牧師。只是,康斯特勃十分確定他要成為一名畫家,且立志要忠於這領受。但雖如此,他仍願意幫助父親管理磨坊多年,在期間,他一直抽空作畫,將居所附近的所有景物,包括熟悉的牛羊、風車、磨房等都畫遍。後來,他遇到一位業餘風景畫家,在他的指導下,康斯特勃的畫技得到很大的提昇。 進而在1799年,考入英國藝術的最高學府「英國皇家美術學院」,與特納成為同窗。
在美術學院的日子,他意圖摹仿大師們的風格,但並不成功,在失意之間,甚至想回鄉干脆做個磨房主算了。不過,當他回過神來,他還是發現自己熱愛畫畫,只是,與其臨摹古典風景畫,不如向大自然學習,唯有親自浸泡在偉大奇妙的大自然中,才能真正將它的美表現出來。
康斯特勃的一生簡樸平淡,小康之家,天資聰穎,卻鬱鬱不得志。 23歲考入了英國皇家美術學院,但到了43歲,才以《The White Horse》這幅畫成為皇家學院準院士,而要到了54歲,才成為英國皇家美術協會的正式會員。更為婉惜的是,康斯特勃至愛的太太在他成為正式會員的前一年病逝了,沒能親眼看到他「成功」的那一天。
The White Horse,1819
在大自然和生命中的真誠與堅持
康斯特勃熱愛家鄉和大自然,他猶如一位田園詩人,把英國的風景畫真正從因襲成規和外國影響中擺脫出來。他以純樸的現實主義自然觀向人們展現明淨的大自然,畫裡沒有隱藏的思量或哲理的暗示,在他筆下,田園如此之真。他就是一心一意地用筆觸和色彩表現在大自然中的,那特定的光線、特定的時間和特定景色裡,用語言傳達不了的東西。他主張要去到生活的源頭「大自然」去尋求完美,故被公認為是最誠實的大自然的謳歌者。
他的作品格調清新活潑、感情真摯、色調明快,充滿自然生氣和鄉土氣息。他為了畫好雲朵,會像個氣象學家一樣仔細觀察雲朵在不同天氣下的形狀,不斷創作出有關雲的作品。康斯特勃的作家朋友曾如此寫到:「看到康斯特勃畫的雲,讓我有一種想穿上大衣帶上傘的衝動。」在看到這些雲時,讓人彷彿置身一片廣闊無垠的天空下,無論是波瀾壯闊般的暴風雨前,還是寧靜安詳的藍天白雲,抑或是在火熱強烈的夕陽輝映下,他都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康斯特勃至終堅持著自己的繪畫風格,堅持走自己的創作道路,而他的這份追求真摯、忠於自己的「執著」,也反映在其與妻子瑪利亞忠貞不渝的愛情上。康斯特勃喜歡家鄉,更喜歡與他青梅竹馬的瑪莉亞,但因女方的父親不同意他們的結合,他用了5年的時間拚命工作,來證明自己的誠意和成家的能力。他曾對他的妻子說:「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改變或淡化我對你的愛,愛你已經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無論任何艱難險阻。」結果,他得償所願,與瑪莉亞在聖馬田教堂成婚,婚後生養了7個孩子。
同向大自然致敬
特納和康斯特勃同被譽為19世紀上半葉英國學院派畫家的代表。 他們的個性、際遇和人生都截然不同,但對於大自然、造物主和他們的繪畫生命,他們同樣是獻上了無比的讚嘆、敬意和忠誠,在美術發展的長河上,留下真摯美麗的神彩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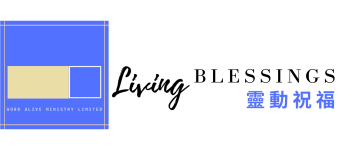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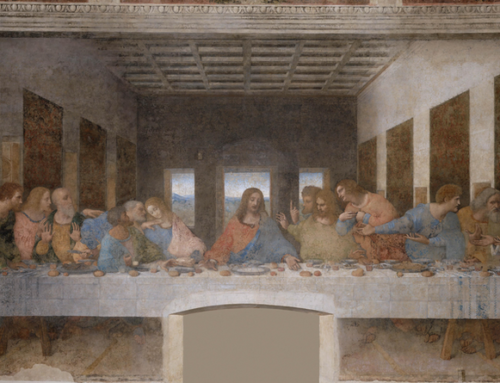
神與人相遇-500x383.jpg)
-500x383.png)